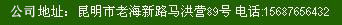|
水均益采访普京时,普京给他的拥抱通过央视全国皆知,大家不知道的是,他们采访时用的灯,都是向BBC借的。(长江文艺出版社供图/图) 马航事件之后,我也想直接就到现场,但我走不了。写报告、办签证……15天之内你能出发算你牛; 这么多年,我没变成老油条,心中还怀着对新闻的执著和追求,甚至是一往直前; 我把心剖给你看。 ——水均益 对于水均益来说,央视无限庞大,但从很多技术环节上看,就是“一个小作坊”。 年1月17日,水均益在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现场采访普京,这是他第五次采访俄罗斯总统。 采访是俄罗斯总统新闻局邀请的,因为索契冬奥会受到西方国家抵制,西方国家领导人拒绝出席冬奥会。专访结束前,普京对着摄影机,张开左臂,给水均益来了一个拥抱。 “我都没好意思说,那次我们是找BBC借的灯。”年4月30日,水均益在北京亦庄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满是无奈。 摄像师不配灯,需要用灯,要打报告申请,运气不好,有可能这个报告要半年后才批准。“还不如自己在淘宝上掏钱买了”。 类似的事情很多,马航事件,水均益也想第一时间冲到现场,但哪怕动用各种私人关系,最快速拿到签证,也要至少15天。 这次采访普京,从得到通知,到台里审批、拿到签证,用了27天——他出发前一天晚上10点多拿到的签证。 从年至今,水均益在央视做过很多节目。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到《世界》、《国际观察》,从《高端访问》到《》、《环球视线》。 年4月,水均益的新书《益往直前》出版,书中记录了他在央视15年的光鲜,也有15年的委屈:参与国际新闻竞争多年,面对新闻理想与现实冲突时却有种种无奈;专访四百多位名人政要,却最终面对《高端访问》被撤销的悲哀;亲历伊拉克、阿富汗战场,奉命必须撤退,却被网友误解为“伊战逃兵”饱受唾骂…… 水均益说自己什么都可以“翻篇”,都可以“忘记”,唯独耿耿于怀《高端访问》“被消失”。年新闻频道改版,《高端访问》莫名地渐渐消失了。“没人通知我,也没有人说原因,就这样没有了。” 在央视的二十年,水均益和他的战友白岩松、崔永元一样,表面风光,衣着光鲜,有着“无法向外人道”的无奈。跟崔永元选择离开不同,“规矩”惯了的水均益还是选择坚守央视。 “你离开这个平台上哪儿去?你是做国际新闻的,离开央视,哪里有这样一个平台?” 我把心剖给你看。”水均益摊开《益往直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年5月,央视主持人(左起)敬一丹、倪萍、水均益、鞠萍。(CFP卢北峰/图) “我们一度心花怒放” 南方周末:《东方时空》的几大总主播,现在只剩下你和白岩松了。 水均益:小白(白岩松)可能还好点,他的实力和能力放在那里。我们都说,他得当官,可他不愿意做官,他早年连一个制片人都辞了。中国的事就是这样,哪怕你再大腕,依然是一个技术人员,一个业务干部。 但一些国内重大新闻主持机会,也不是都给他的。不是他不愿意干,也不是有人给他使绊,就好像有种无形的力量,让他不能全面施展才华。 南方周末:你是怎么成为“总统采访专业户”的? 水均益:其实是无心插柳形成的习惯。第一次是我在《东方时空》采访基辛格,有那个年代的优势,比如会说外语,知道点国际的事,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采访总统专业户。但我知道,很多总统接受你采访不是因为你是水均益,是因为你是CCTV。有的人还不接受你采访,比如奥巴马来的时候就不接受我的采访。 南方周末:年,你到《东方时空》工作。这21年可以划成两段,前十年,后十年。你怎么看在央视工作的二十年? 水均益:套用小白的书名,《痛并快乐着》。这当中有点点滴滴的快乐,有的甚至是很短暂的瞬间,更多是一种探索过程,一种挣扎的过程。 《东方时空》这一代人,严格说是中国电视新闻的一个层面,这个层面的人,都怀着对电视新闻的追求。那个时候给我们的平台,让我们一度心花怒放,热血沸腾。 实际上,这二十年,我和很多其他同行,更多时候是在纠缠于当时的短暂瞬间,迷恋那样的短暂瞬间,依依不舍于那个短暂瞬间。我相信小白也差不多,遇到挫折,遇到打击的时候,我们会很本能地在那些短暂灿烂中寻找慰藉,让我们坚持下去。 年的中央电视台,和年的中央电视台,你不能否认,从硬件到报道面,都在进步。但从新闻的深度追求来讲,没有跨越式的质的飞跃,但总体上还在缓慢上坡。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慢了点,可能有人觉得不够,但是你又能怎么办呢? 南方周末:新闻频道开播,我在央视待了两天,亲见你们的热情(详见年5日南方周末《新闻频道来了》)。 水均益:年5月,我们这批人终于有了自己的阵地,每个人都是雄心勃勃,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新节目。拥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是所有当时做新闻的人的梦想,我们对那个平台寄予了很大的期待,但整个事情的发展……我也很难理解。 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国家的事业单位,不能说它是简单的国企,它带有我们中国体制内的所有单位的轨迹和色彩,这不是央视特有的,你也不能说,央视怎么不改革? 在这二十年里,这种事不是发生一次,我们身在其中,有时候也很无奈,有时候也在期待。 、年,有一段时间,我几乎灰心丧气了,我那时候的能量,可能只发挥了10%、20%,像空有一身功夫的高手,无处施展。 你是一个记者、一个主持人,你最大的舞台就是CCTV,人家不用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跟谁去哭诉。电视非常现实,不给你机会,时间不用长,只用两年,观众就能把你忘得干干净净。 在央视,你就是一个可以替代的零件。 “唯独《高端访问》我还在纠结,为什么被取消?” 南方周末:在外界看来,你在央视应该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 水均益:电视是一个喜新厌旧的行当。相比女主持人,男主持人好一点,但也是有限的。我陷入低潮的时候,小白偶尔跟我喝上两杯酒,他拍拍肩膀说,老哥呀,我理解你。 我在书里也写到了,包括所谓“央视风云二十年”,包括《高端访问》的成立,以及它最后的消失,或者说半消失。我是特别善于忘记的人,很多事情翻了篇就翻了篇,我不会再纠结了,但是《高端访问》这件事,我至今还在纠结。 我不理解,为什么?《高端访问》是多好的品牌节目。差不多是突然说没就没了,中间挣扎过一段,领导也说你可以不定期播出,可以在底下小角上打一个“高端访问”,但是性质变了。 电视是一个约会制,没有固定的平台,没有固定的时间,没有实打实的品牌的时候,《高端访问》就自然而然消失了。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消失? 水均益:不知道。我有一次跟小白聊这个事,我们都很迷茫。 我在中央电视台二十多年,各级领导总体来讲是在支持我的,也在拿你当一个非常优秀的记者在用。 这次我去索契采访普京,拿到了独家采访,全电视台,从《新闻联播》到《新闻直播间》,直到各档的早间新闻,都是铺天盖地在用。各级领导,在各种会上,完全不惜笔墨地在表扬我。 这让我感到受宠若惊,有时候想想,我快退休了,人家依然重视你,你只要干出好东西,领导也好,同事们也好,还是很认可的。你有什么怨气可撒? 我又觉得,为什么《高端访问》要被取消掉? 年,新闻频道成立6年了,要改版,电视台这种改版,跟沿海企业品牌创新一样,是时不时的。来一个新领导,要改一下;或者干了一段时间,大家觉得腻了烦了,改版。 我们最近又在改版,改版是一种创新,我不否认,但我们身在其中的人觉得这是很恐怖的事。每次改版,比生个孩子还痛苦。要研发、出主意,一遍一遍折腾,当然这是必然的。如果你的节目已经被黄牌警告三次,没人看你的节目,必须拿下,那改是应该的。但很多栏目不是这样,从底下人来讲,节目挺好,那改它干什么呢?也没有说:“水均益同志,我跟你谈一下,这个栏目我们取消了,理由我把证据全都摆好。”没有,给你打个电话,通知你一下,就很不错了。 南方周末:《高端访问》就是这样“被消失”了? 水均益:也许很多人觉得,水均益你在电视台是响当当的人物,可以直接推开台长的门,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就是干活的人。我当然好点,还兼个栏目制片人,但也还是个兵头将尾,也是被通知的。 听到要停掉,我五雷轰顶,为什么?给我的解释是,新闻性不够。我采访的很多人是总统,不是韩国客船的船长,不是马航负责调查的希沙姆丁,你播一个法国总统,或者是加拿大总理,他认为这是新闻性不够强。 我说这是中央电视台的品牌,你看一下,CNN、BBC,哪一个国外的新闻大台,不都有类似的品牌吗?这些品牌人家一干就干30年,不会说新闻性不够。 你十年之后采访到本·拉丹,你说难道不是新闻吗?现在你采访波兰总统,难道不是新闻吗? 当时的领导给了我一个折中说法,把时间缩短,别每次采访四十多分钟,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弄二十分钟半小时。我当时多多少少接受了妥协方案,而且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领导说的,《高端访问》这个番号留着。 我当时的想法,这个牌子要留着。哪怕两周、三周播一次,我可以提前预告。结果实际操作时,《高端访问》慢慢被弱化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被通知,《高端访问》的栏目代码取消了。 南方周末:没法解决吗? 水均益:完整和成熟完善的新闻频道,应该有专栏,像BBC,恨不得一年就拍一个专题片。可现实是,我们做不了。 年之后,新闻频道大发展,强力推行碎片化、资讯化、短平快,这种策略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中国很多事情往往容易走极端,要求“去栏目化”,结果《纪事》、《百姓故事》、《高端访问》……统统没有了,等于完全退回原始状态。 好的东西,好的土壤,一旦被毁掉,你想重新把它建起来,是很难的。当一个马力十足的火车头开起来,你突然让它停下来,或者说突然让它拐一个大一点的弯,很难。 “我们被收视率逼的” 南方周末:在央视的新闻节目里,国际新闻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水均益:长期以来,国际新闻处于边缘化的状况,或者说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我在《焦点访谈》的时候,节庆日和一些特殊日子,国内题材没法做,就跟我说,那就多做几期国际吧。从重视上来讲,比如从国际新闻节目的经费,人员的配置,包括栏目时段安置,最后的所谓考评来看,概念里面没把你作为主流,这是持续多年的。 南方周末:国际新闻的尺度是不是比国内新闻大? 水均益:这是个误区,以为国际新闻比国内新闻更开放一些,报道的空间更大,其实完全不是。 到了这个时代,新闻不应该被简单划为国际和国内了,很多事情是国内国际跨界的。马航这个事,你算国际还是国内。 对比以前,现在还是有了进步,以前是一刀切,直接不能做。“9·11”的时候,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在现场直播,我们个个都跃跃欲试要上,但只能看着那个楼在烧,要塌。最后一律不能播,小白(白岩松)也有这个体验。“9·11”发生的时候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多,我一直扛到早上六七点,天亮了。等到最后确认没戏了,才悻悻然回家。 南方周末:理由是什么呢? 水均益:不好拿捏。央视是国家电视台,代表中国的态度,可能会引发外交层面的问题;再后来的伊拉克,包括后来的叙利亚、埃及,逐渐逐渐好一点,可以直播,做个三五天。 这些新闻往往跟我们的对外政策、对外立场有关,各种各样的平衡、权衡、考量有关。你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反过来从新闻角度讲,你又会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只是一个节目,至于吗? 南方周末:这时候怎么说服自己? 水均益:我在央视工作二十多年,从新华社工作算起,我参加工作快30年了,我努力地在理解,努力地在适应。这么多年,我没变成一个老油条,还怀着对新闻的执著和追求,甚至是一往直前的感觉。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首先,老百姓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国际新闻的市场越来越大,各种媒体,无论中央媒体、地方媒体,包括网上的媒体,都在努力适应这个趋势。各级都渐渐领受到老百姓的需要。 我们做的是新闻,当然希望它符合新闻规律,但是事实上,你又不能。无论《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是中央电视台,我们不能摆脱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国家电视台,我们是国家通讯社,我们是党报。哪怕你说“本台观点不代表外交部观点”,外媒和外国政府依然会拿你的新闻报道当官方表态。往往纠结就在这里。 南方周末:国际新闻已经成为下一个新闻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同类节目出现了。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水均益:国际新闻现在是热点,但我们好多老百姓,其实是选择性地接受信息,而且想当然地认为,世界就是那样。 我做《环球视线》时特别有体会,我们一度被收视率逼的,只有做枪长炮短,比如我们一个歼20,一个军演,或者我们跟日本在钓鱼岛上的问题,跟菲律宾在黄岩岛上的节目,收视率噌地就上去了。 收视率的压迫会影响你对新闻的选择,让你不得不去北京哪个医院治白癜风最好北京治疗白癜风一般需要多少钱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仇和十年全纪录nbsp南方周末
- 下一篇文章: 阜宁新闻今日看点顾云岭接受江苏电视